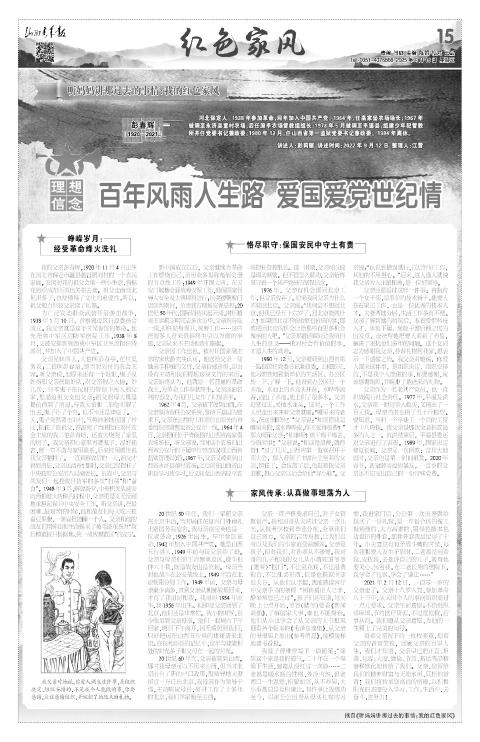百年风雨人生路爱国爱党世纪情
彭春辉(1920—2021) 河北保定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任高家堡农场场长;1967年被调至永济县董村农场,后任原平农场管教组组长;1973年5月被调至平遥县,组建少年犯管教所并任党委书记兼政委;1980年12月,任山西省第一监狱党委书记兼政委。1984年离休。
讲述人:彭莉丽 讲述时间:2022年9月12日 整理人:江雪
峥嵘岁月:经受革命烽火洗礼
我的父亲彭春辉,1920年11月4日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蠡县蠡吾镇刘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农闲时我的祖父会做一些小生意,将棉花纺织成布匹再出关东去卖。祖父走南闯北见识多了,也便懂得了文化的重要性,所以,祖父勉力供我父亲读了私塾。
为广泛发动群众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我父亲就是这个时候参加的革命。他先在冀中军区后防军医院工作,1938年8月,又被安排到冀西冀中军区卫生部担任特派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兄妹四人,大伯叫彭春亭,在村里务农;二伯叫彭春培,是当时刘村的农会主席。听父亲说,他原来还有一个姐姐,鬼子汉奸得知父亲在锄奸队,对父亲恨之入骨。好几次,日本鬼子在汉奸的带领下闯入祖父家,想逼迫祖父交出父亲;祖父祖母大概是提前得到了消息,与我大伯和二伯他们躲了出去,鬼子扑了个空。但不幸还是降临了。一天,鬼子突然袭击刘村,气势汹汹地包围了村庄,抓住了我祖父,并害死了当时担任刘村农会主席的我二伯彭春培,还放火烧毁了家里的房子。我父亲担心家里再遭鬼子、汉奸祸害,便一直不敢与家里联系,后来村里就传说我父亲牺牲了。一直到解放后的一天,祖父才得到消息,父亲还活着!那时,父亲已经担任了中央政府公安部八局副处长。抗战中,父亲与战友们一起挫败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和“蚕食”。1948年3月,解放新夕,中央机关从延安向西柏坡大转移的过程中,父亲更是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保卫中央安全工作。听父亲讲,在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他和战友们每天吃三粒蚕豆果腹,一条扁担能睡一个人。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被毛泽东誉为“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模范区”的安宁。
恪尽职守:保国安民中守土有责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继续为革命工作燃烧自己,亲历众多堪称彪炳史册的节点性工作:1949年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全面统筹安保工作,确保国家领导人安全及大典顺利进行;抗美援朝板门店谈判期间,负责我方现场安保总控;20世纪50年代,国际局势风起云涌,时任越南主席胡志明同志多次访华,父亲均身临一线,担任贴身保卫、统筹工作……这些在很多人看来值得终生引以为傲的事迹,父亲从来不主动和我们提起。
父亲因工作出色,被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先生认可,她送给父亲一盆她亲手种植的文竹,父亲倍感珍惜,却也没有主动和我们提起这盆文竹的来历。父亲始终认为,他就是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为革命工作奉献终生。父亲淡泊名利的态度,为我们儿女作了积极表率。
1962年4月,父亲被下放到山西,在父亲坚持留任公安系统、坚持下基层的要求下,父亲在山西的工作单位由原先的省委组织部调整至省公安厅一线。1964年4月,父亲担任位于清徐县的山西省高家堡农场场长。听父亲说,当时这个农场归山西省公安厅的下属单位劳改局(现山西省监狱管理局)管。1967年,父亲又被调到山西省永济县董村农场;之后前往山西省山阴县学习班学习,后又调至山西省原平农场担任管教组长。这一时期,父亲可以说是调动频繁。但不管怎么调动,父亲始终坚守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信念。
1976年,父亲有机会调回北京工作,但父亲放弃了。后来我问父亲为什么不调回北京。父亲说:“我何尝不想回北京,但我已经五十六岁了,回北京能做什么?如果回北京不能做更有价值的事,那就把回北京的机会让给那些有更多机会做事的人吧。”父亲那番话瞬间让我明白人生的意义——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才是人生的真谛。
1980年12月,父亲被调到山西省第一监狱担任党委书记兼政委。上班那天,他习惯性地到新单位的生活区、办公区转一下、了解一下。他看到办公区有一个水池,水池上的水龙头开着,水哗哗流着,溢出了水池,地上积了很多水。父亲赶紧过去,关掉水龙头。这时,一个工作人员走出来冲着父亲就嚷:“哪里来的老头,在这里瞎转!”父亲说:“你别管我是哪里来的,这水哗哗流,你不觉得浪费?”那人呵斥父亲:“你谁啊?该干吗干吗去,少管闲事!”父亲说:“你这是浪费,就得管!”过了几天,山西省第一监狱召开干部大会,那人看到了主席台上坐着的父亲,愣住了。会议散了后,他赶紧找父亲道歉,担心父亲以后会给他“穿小鞋”。父亲说:“认识到错误就行,以后好好工作,其他的不用担心。”后来,这人逢人就说我父亲为人正派和善,是一位好领导。
父亲还提起过这样一件事:省监有一个女干部,是单位的技术骨干,她爱人在石家庄工作,也是一位优秀的技术人才。夫妻两地分居,生活工作多有不便。父亲了解到她的情况后,本着爱惜科技人才、体恤下属、免除干警后顾之忧的出发点,设法帮她把爱人调到了省监,解决了困扰他们多年的问题。这个女同志为感谢我父亲,拎着礼物到我家,想表示一下感激之情。我父亲对她说,你爱人调来这件事,是组织决定、组织安排的,不是我个人能做的事,你要感谢,应该感谢组织,并婉拒了她送来的礼物。
父亲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也一直积极践行社会责任。1977年,平遥发洪水,父亲第一时间带人救灾,又捐出了一百元钱。母亲当时也捐了五十斤粮票。要知道,当时一个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八块钱。我父亲是那次全县捐款最多的人之一。抗洪结束后,平遥县委还对父亲进行了表彰。1989年,国家决定修复长城,父亲又一次捐款;汶川大地震时,父亲也是第一时间捐款。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百岁的父亲还不忘交出自己的一份特殊党费。
家风传承:认真做事坦荡为人
20世纪50年代,我们一家随父亲在北京生活,当时居住在复兴门外南礼士路国务院宿舍。我母亲徐宝英也是一位老革命,1926年出生,早年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是山西五台县人,1949年前与我父亲结了婚。父亲与母亲相识于晋察冀边区,携手相伴六十载,既是战友也是伉俪。母亲当时也战斗在公安战线上。1949年后在北京朝阳分局工作。1949年前,父亲与母亲聚少离多,直到父亲从朝鲜战场回来,才有了我哥哥和我。我哥哥1954年出生,我1956年出生。但即使父亲回到了北京,他们还是非常忙。我小的时候,很少能见到父亲母亲。他们一般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离开,因无暇照顾我们,只好把远在山西五台县的姥姥请来北京。在我和哥哥的记忆中,童年与姥姥相处的时光多于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
20世纪60年代,父亲被调到山西。那时我母亲可以不用来山西,但当时北京出台了新的户口政策,鼓励异地夫妻留京一方迁出北京,我母亲作为领导干部,主动响应号召,离开工作了十多年的北京,我们举家搬至山西。
父亲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对子女管教很严。我和哥哥从未沾过父亲一点儿光,从报考学校到毕业分配,全靠我们自己努力。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小家庭受益颇深。父亲爱孩子,但对我们、对孙辈从不溺爱。我哥哥的儿子和我的女儿从小就知道爷爷(姥爷)“抠门”,不让乱花钱,不让浪费粮食,不让乱丢东西,但是他捐款时却很大方。从他们认字起,就能熟读客厅中父亲手书的条幅 “闲谈莫论人之非,静坐常思己之过”。孩子们还知道,每天晚上七点开始,爷爷(姥爷)要看《新闻联播》,了解国家大事,谁也不能换台。他们从小也学会了从父亲的大书柜里翻看各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从父亲的书报架上抽出《参考消息》,像模像样地读书看报。
我嫂子曹琳曾写下一篇随笔:“嫁到这个家是我的福气。二十年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婆媳从没红过一次脸……二老都是暖水瓶的性格,外冷内热,但老两口一生恩爱,相敬如宾,从不吵架,大小事都总是互相谦让。有件事让我感动至今,以前公公出差从没买礼物的习惯,我进家门后,公公第一次出差就给我买了一份礼物,是一件很合体的做工极精细的、大方高雅的、墨绿色镶本色边盘扣的外套。那件外套我足足穿了十年。小夫妻总有有矛盾斗嘴的时候,每次我和爱人发生矛盾时,二老都是向着我、安抚我,去批评自己的儿子,教育他要关心、包容我。在二老长期的熏陶下,我学会了包容,学会了谦让……”
2021年2月12日,一百零一岁的父亲走了。父亲十八岁入党,参加革命八十三年,从未因个人的事向组织提过一点儿要求。父亲生前遗愿:不给组织添麻烦,节约医疗资源,不过度抢救,后事从简。我们遵从父亲遗愿,为他的一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看着父亲留下的一枚枚奖章,想着父亲的音容笑貌,回顾父亲的百岁人生,我们才知道,父亲早已把正直、坦荡、包容、大度、勤俭、节约、豁达等品格潜移默化地传给了我们。父亲,您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与天地永恒,同松柏常青!我们将传承您高尚的情操,以积极阳光的态度投入学习、工作、生活中,去奋斗,去努力!
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