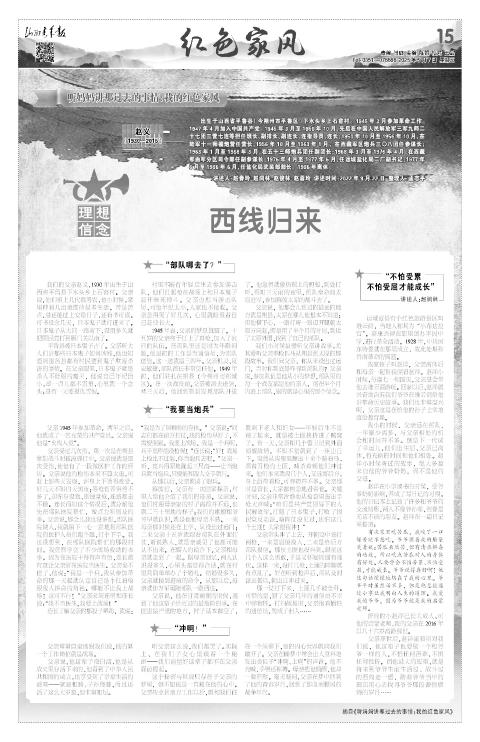西线归来
赵义(1930—2016) 出生于山西省平鲁县(今朔州市平鲁区)下水头乡上石窑村。1945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3月至1950年10月,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九师二十七团三营七连等担任班长、副排长、副连长、连指导员、连长;1950年10月至1956年10月,在陆军十一师榴炮营任营长;1956年10月至1963年1月,在西藏军区炮兵三○八团任参谋长;1963年1月至1968年3月,在五十三师炮兵团任副团长;1968年3月至1976年4月,在西藏那曲军分区司令部任副参谋长;1976年4月至1977年6月,任运城盐化局二厂副书记;1977年6月至1986年6月,任盐化局武装部部长。1986年离休。
讲述人:赵春玲 赵润林 赵俊林 赵蓉玲 讲述时间:2022年9月22日 整理人:孟志平
“部队哪去了?”
我们的父亲赵义,1930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鲁县下水头乡上石窑村。父亲说,他们祖上几代都务农,他小时候,家里种着几亩地维持基本生活。苦是苦点,总还能过上安稳日子,还有书可读。可书没念几天,日本鬼子就打进来了。日本鬼子从大同一路南下,没用多久就把国民党打到雁门关以南了。
平鲁县被日本鬼子占了。父亲听大人们讲那些日本鬼子如何凶残,他也知道周围各县都有村民遭到鬼子欺凌杀害的事情。在父亲眼里,日本鬼子就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说自己年纪虽小,却一点儿都不害怕,心里就一个念头:总有一天要报仇雪恨。
村里不断有年轻后生去参加游击队,他们扛起枪在战场上和日本鬼子展开殊死搏斗。父亲也想当游击队员,可他年纪太小,人家也不接收。父亲急得哭了好几次,心里就盼望着自己赶快长大。
1945年春,父亲的梦总算圆了。十五岁的父亲终于扛上了真枪,加入了抗日的队伍。在部队里还是因为年龄问题,他最初的工作是当通信员,为部队送信。这一送就是三四年。父亲机灵,反应敏捷,部队首长非常信任他。1949年初,他们驻扎在朔县 (今朔州市朔城区)。在一次战役前,父亲被派去送信,两三天后,他回到朔县发现部队开拔了。他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打听,得知三天前的夜里,部队奉命向太原进军,参加解放太原的战斗去了。
父亲说,他那会儿到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朔县,太原在哪儿他根本不知道;但他横下心,一路打听一路迈开腿朝太原方向赶,愣是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到达了太原外围,找到了自己的部队。
我们小时候最爱听父亲讲故事,尤其爱听父亲单枪匹马从朔县到太原的那段故事。我们问父亲,你从来没出过远门,当时你到底是咋寻到部队的?父亲说,参加队伍是他从小的梦想,部队里的每一个战友都是他的亲人,能在半个月内追上部队,靠的就是心里的那个信念。
“我要当炮兵”
父亲1945年参加革命,两年之后,他就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父亲说他是“火线入党”。
父亲受过几次伤,第一次是在朔县参加战斗时被流弹打中。父亲说就是那次受伤,使他有了一段做医护工作的经历。父亲说他的枪伤本来不算太重,可赶上那些天发烧,浑身上下烫得难受,好几天不知白天黑夜;等枪伤养得差不多了,却浑身没劲,别说拿枪,连路都走不稳。连长得知这个情况后,就分派他先在部队医院帮忙,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父亲说,那会儿我也没多想,部队医院缺人,我就留下一心一意地帮部队医院的医护人员们跑个腿,打个下手。我也没想到,在部队医院帮忙的那段时间,我竟然学会了不少战场救助的本事。因为在医院干得有声有色,连长就有意让父亲留在医院当医生。父亲坐不住了,他说:“我是一个兵,我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认定自己是个扛着枪跟敌人拼命的角色。哪能不让我上战场!这可不行!”父亲来到连里和连长说:“我不当医生,我要上战场!”
连长了解父亲的那股子犟劲,就说:“我是为了照顾你的身体。”父亲说:“同志们都在前方打仗,我的枪伤早好了,不需要照顾。我要上战场,我是一个兵啊,兵手里咋能没枪呢!”连长说:“好!战场上枪比不过炮,你当炮兵去吧。”父亲一听,高兴得原地蹦起三尺高——让当炮兵就当炮兵,只要能和敌人交手就行。
从那以后,父亲就成了炮兵。
解放后,父亲有一次回家探亲,村里人给他介绍了我们的母亲。父亲说,他们村跟母亲家的村子离得并不远,也就二三十里地的样子;我们的姥娘和爷爷早就认识,就是他和母亲不熟。一来母亲那时候还在上学,从没出过远门;二来父亲十五岁就跟着部队在外面打仗,甭说熟人,就是亲戚见了他都可能认不出来。在媒人的说合下,父亲和母亲就走到了一起。据母亲回忆,两人认识没多久,心里头都觉得合适,就在村里简简单单办了个婚礼。结婚没多久,父亲就接到进藏的命令。从那以后,母亲就作为军属随部队一路西进。
父亲说,他在甘肃剿匪的时候,遇到了他这辈子经历过的最危险的事。在匪患最严重的地方,村子基本都空了,就剩下老人和妇女——年轻后生不是藏了起来,就是被土匪挟持进了贼窝子。有一天,父亲和几个警卫员到外面侦察敌情,不知不觉就到了一座山丘下。突然从沟壑里蹿出十来个骑着马,握着刀枪的土匪,喊杀着朝他们冲过来。他们本来就没几个人,又远离后方,身上虽带着枪,可弹药并不多。父亲那时是营长,大家都焦急地看着他。关键时刻,父亲非常冷静地从枪套里拔出手枪大声喊:“咱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打跑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啥阵仗没见过,还怕这几个土匪!大家跟我冲!”
父亲带头冲了上去,并朝空中连打两枪,一来是震慑敌人,二来是给后方部队报信。那伙土匪也没料到,眼前这几个人这么勇敢,于是又怀疑周围有埋伏。这样一来,没打几枪,土匪的阵脚就有点乱了。好在听到枪声后,部队及时派出援兵,朝山丘冲过来。
那一仗打下来,土匪几乎被全歼。可惜的是,跟了父亲几年的通信员不幸中弹牺牲。打扫战场时,父亲抱着牺牲的通信员,哭成了泪人……
“冲啊!”
父亲常常自豪地跟我们说,他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战场。
父亲说,他这辈子没白活,他是从战火里存活下来的,他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享受到了幸福生活的滋味——家庭和睦、子孙绕膝,而且还活了这么大岁数,他非常知足。
听父亲这么说,我们都笑了。实际上,在我们子女心里藏着一个秘密——我们商量好这辈子都不在父亲面前提起。
这个秘密与其说只存在于父亲的梦里,倒不如说是一直藏在他的心中。父亲转业到地方工作以后,就和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他的内心世界就向我们敞开了。父亲在睡梦中常会出人意料地发出类似于“冲啊、上啊”的声音。他不光喊,手臂还挥舞。母亲把他摇醒,他却一脸茫然。毫无疑问,父亲在梦中回到了他的青春岁月,回到了那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
“不怕受累不怕受屈才能成长”
讲述人:赵润林
运城夏县有个红色旅游景区叫堆云洞,当地人称其为 “小布达拉宫”。嘉康杰曾在那里创办平民中学,进行革命活动。1928年,中共河东特委就在那里成立,故此处堪称晋南革命的摇篮。
我家孩子叫赵洋,父亲离休后和母亲一起帮我照看赵洋。赵洋小时候,每逢七一和国庆,父亲总会带他去堆云洞游玩。回家以后,赵洋就兴奋地告诉我们爷爷在堆云洞给他讲革命历史故事。我们也非常高兴啊,父亲这是在给他的孙子上实地政治教育课。
我小的时候,父亲远在部队,一年聚少离多,与父亲相处的机会和时间并不多。倒是下一代成了幸运儿,他们出生后,父亲已离休,有充裕的时间和他们相处。赵洋小时候听过的故事,绝大多数来自他的爷爷奶奶,而不是他的父母。
赵洋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受爷爷奶奶影响,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本上记载了许多和爷爷的交流情形,两人不像爷孙辈,倒像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赵洋在一篇日记里提道:
有次家里吃苦瓜,我咬了一口嫌苦就不想吃。爷爷摸着我的脑袋笑着说:苦瓜虽然苦,但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所以吃点苦瓜对人的身体有好处。人要学会不怕苦累、不怕受屈,才能成长。爷爷说得真好啊!他这句话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爷爷平时虽然话不多,但是他总能通过小事让我明白人生的道理。我爱我的爷爷,因为爷爷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曾经的小赵洋已长大成人,可他的启蒙老师、我的父亲在2016年以八十六岁高龄辞世。
父亲辞世后,赵洋流着泪对我们说,他这辈子也要做一个和爷爷一样的人,不怕任何苦难,不惧任何挫折。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到爷爷生前生活过、战斗过的西线走一遭,踏着爷爷当年的脚印用心去找寻爷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