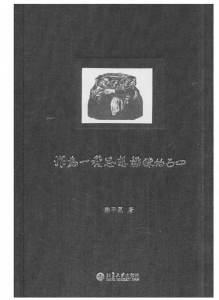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陈平原教授的治学领域从小说史研究,渐次拓展至学术史、教育史等领域,气象与规模日趋阔大,然而无论研究对象如何转换,“五四”始终是他自觉直面并着力经营的课题,是他探索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坐标和参照系,也是他借以介入当代思想讨论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从标题可以看出,这本小书包含了作者讨论“五四”的某种方法论层面上的思考。同时,它也是针对当下文化思潮的有感而发之言。
书名: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作者:陈平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陈平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著有《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千古文人侠客梦》《读书的“风景”》等著作多部。
内容简介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是作者专论“五四”的一本书,收录十一篇文章,文章长短及体例不一,有论文,有随笔,也有答问。只是在将“五四”作为思想的磨刀石这一点上,取共同立场。答问部分夹杂个人阅历与感受,明显带有主观性。可即便是专业论文,也都是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相互缠绕。“五四”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
书摘
一百多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是一代代人成长史上必不可少的精神坐标。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来说,与“五四”对话,是研究专业,更是自己的生命形态。《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收录了陈平原专论 “五四”的论文、随笔、答问等篇章。十年前,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导言”中说过:“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十年后重读这段话,我依旧坚持此立场,谈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是“五四”;第二,风雨兼程说“五四”;第三,“走出”还是“走不出”;第四,如何激活“传统”。
为什么是“五四”
晚清以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代代中国人奋起搏击,风云激荡中,出现众多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有的如过眼云烟,有的欲说还休,有的偶尔露峥嵘,有的则能不断召唤阅读者与对话者——“五四”无疑属于后者。五四运动的规模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为何影响竟如此深远?我用以下三点理由,试图作出解释。
第一,五四运动的当事人,迅速自我经典化,其正面价值得到后世大部分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认可。可以这么说,“五四”成了近百年来无数充满激情、关注国家命运、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青年学生的“精神烙印”。
第二,五四运动虽也有“起承转合”,但动作幅度及戏剧性明显不如八年抗战。不过,后者黑白分明,发展线索及精神维度相对单纯,不像前者那样变幻莫测、丰富多彩。谈论“五四”,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思想学说,还不如说是这种 “百家争鸣”的状态让我怦然心动、歆羡不已。
第三,某种意义上,五四运动的意义是“说出来”的。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
风雨兼程说“五四”
说“五四”不仅仅是历史事件,更是近百年中国读书人重要的思想资源、极为活跃的学术话题,甚至可以作为时代思潮变化的试金石,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接受。美国学者舒衡哲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六章“五四的启示”中,辨析新中国成立后官方对“五四”的看法及诸多纪念活动和回忆文章,还有同时期知识分子的抉择与挣扎。这一章的结语很悲壮:“‘五四’不只被看作鼓舞知识分子勇士的精神食粮,它将成为照亮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的一把‘火炬’。”
近百年中国的风风雨雨,让我辈读书人明白,谈论“五四”,不管你是沉湎学问还是别有幽怀,都很容易自动地与现实政治挂钩,只不过有时顺风顺水,有时则难挽狂澜。之后,我选择在进京读书30年这个特殊时刻,盘点零篇散简,凑成一册小书,交给北大出版社以纪念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杂志 《新青年》(1915—1926年)创刊一百周年。当时绝对想象不到会撞上如此“新文化研究热”。之后,我又先后接到十多场纪念“五四”或新文化运动学术会议的邀请,其中,北京大学最为“立意高远”,准备年年纪念,一直讲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一百周年。
“走出”还是“走不出”
如何看待早就沉入历史深处、但又不断被唤醒、被提及的“五四”,取决于当下的政治局势与思想潮流,还有一代人的精神追求。1993年,我曾撰写题为《走出五四》的短文,感叹“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至今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可16年后,我又撰写了《走不出的“五四”?》,称不管你持什么立场,是左还是右,是激进还是保守,都必须不断地跟“五四”对话。从主张“走出”到认定“走不出”(后者虽然加了个问号,实际上颇有安之若素的意味),代表了我对“五四”理解的深入。
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早就翻过去了;而作为精神气质或思想资源的“五四”,仍在发挥很大作用。这本是平常事,为何我会纠缠于“走出”与“走不出”呢?那是因为,五四新文化人的丰功伟绩,某种意义上成了后来者巨大的精神压力。
如何激活“传统”
中国人说“传统”,往往指的是遥远的过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其实,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思想、学术,早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可以这么说,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贴近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之血肉相连,更有可能影响其安身立命。
我并不否认“五四”新文化人的偏激、天真乃至浅薄,但那是一批识大体、做大事的人物,比起今天很多在书斋里条分缕析、唾沫横飞的批评家,要高明得多。在我看来,“五四”可爱的地方,正在于其不纯粹,五彩斑斓,充满动态感与复杂性。
我的基本立场是: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我曾说过:“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 ‘五四’等 ‘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
书名: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作者:陈平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陈平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著有《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千古文人侠客梦》《读书的“风景”》等著作多部。
内容简介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是作者专论“五四”的一本书,收录十一篇文章,文章长短及体例不一,有论文,有随笔,也有答问。只是在将“五四”作为思想的磨刀石这一点上,取共同立场。答问部分夹杂个人阅历与感受,明显带有主观性。可即便是专业论文,也都是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相互缠绕。“五四”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
书摘
一百多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是一代代人成长史上必不可少的精神坐标。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来说,与“五四”对话,是研究专业,更是自己的生命形态。《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收录了陈平原专论 “五四”的论文、随笔、答问等篇章。十年前,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导言”中说过:“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十年后重读这段话,我依旧坚持此立场,谈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是“五四”;第二,风雨兼程说“五四”;第三,“走出”还是“走不出”;第四,如何激活“传统”。
为什么是“五四”
晚清以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代代中国人奋起搏击,风云激荡中,出现众多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有的如过眼云烟,有的欲说还休,有的偶尔露峥嵘,有的则能不断召唤阅读者与对话者——“五四”无疑属于后者。五四运动的规模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为何影响竟如此深远?我用以下三点理由,试图作出解释。
第一,五四运动的当事人,迅速自我经典化,其正面价值得到后世大部分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认可。可以这么说,“五四”成了近百年来无数充满激情、关注国家命运、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青年学生的“精神烙印”。
第二,五四运动虽也有“起承转合”,但动作幅度及戏剧性明显不如八年抗战。不过,后者黑白分明,发展线索及精神维度相对单纯,不像前者那样变幻莫测、丰富多彩。谈论“五四”,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思想学说,还不如说是这种 “百家争鸣”的状态让我怦然心动、歆羡不已。
第三,某种意义上,五四运动的意义是“说出来”的。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
风雨兼程说“五四”
说“五四”不仅仅是历史事件,更是近百年中国读书人重要的思想资源、极为活跃的学术话题,甚至可以作为时代思潮变化的试金石,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接受。美国学者舒衡哲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六章“五四的启示”中,辨析新中国成立后官方对“五四”的看法及诸多纪念活动和回忆文章,还有同时期知识分子的抉择与挣扎。这一章的结语很悲壮:“‘五四’不只被看作鼓舞知识分子勇士的精神食粮,它将成为照亮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的一把‘火炬’。”
近百年中国的风风雨雨,让我辈读书人明白,谈论“五四”,不管你是沉湎学问还是别有幽怀,都很容易自动地与现实政治挂钩,只不过有时顺风顺水,有时则难挽狂澜。之后,我选择在进京读书30年这个特殊时刻,盘点零篇散简,凑成一册小书,交给北大出版社以纪念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杂志 《新青年》(1915—1926年)创刊一百周年。当时绝对想象不到会撞上如此“新文化研究热”。之后,我又先后接到十多场纪念“五四”或新文化运动学术会议的邀请,其中,北京大学最为“立意高远”,准备年年纪念,一直讲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一百周年。
“走出”还是“走不出”
如何看待早就沉入历史深处、但又不断被唤醒、被提及的“五四”,取决于当下的政治局势与思想潮流,还有一代人的精神追求。1993年,我曾撰写题为《走出五四》的短文,感叹“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至今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可16年后,我又撰写了《走不出的“五四”?》,称不管你持什么立场,是左还是右,是激进还是保守,都必须不断地跟“五四”对话。从主张“走出”到认定“走不出”(后者虽然加了个问号,实际上颇有安之若素的意味),代表了我对“五四”理解的深入。
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早就翻过去了;而作为精神气质或思想资源的“五四”,仍在发挥很大作用。这本是平常事,为何我会纠缠于“走出”与“走不出”呢?那是因为,五四新文化人的丰功伟绩,某种意义上成了后来者巨大的精神压力。
如何激活“传统”
中国人说“传统”,往往指的是遥远的过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其实,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思想、学术,早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可以这么说,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贴近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之血肉相连,更有可能影响其安身立命。
我并不否认“五四”新文化人的偏激、天真乃至浅薄,但那是一批识大体、做大事的人物,比起今天很多在书斋里条分缕析、唾沫横飞的批评家,要高明得多。在我看来,“五四”可爱的地方,正在于其不纯粹,五彩斑斓,充满动态感与复杂性。
我的基本立场是: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我曾说过:“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 ‘五四’等 ‘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