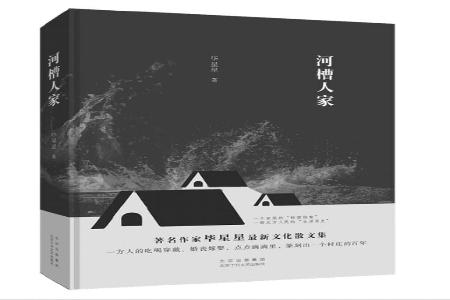总有真情道不得
我和毕星星老师都来自山西晋南地区,晋南地区撤销后,我在临汾市,他在运城市。不管是临汾,还是运城,都属于一个方言语系,说话都是一个味,我的口语往往被人误以为运城人。
都是晋南的,我在吕梁山上,他在汾河盆地的平原上。一个山上,一个山下。我在吃玉米面窝窝头的时候,毕星星吃的是白面馍馍。
言外之意,毕星星所在的平原地区富足,我所在的吕梁山区贫穷。不管富足还是贫穷都属于晋南,属于华夏文明的摇篮。
《河槽人家》于2020年出版,当时举办了一个规模不大但档次较高的研讨会,我应邀参加。时隔数年再搞读书分享会,足见这部散文集的价值。
这部散文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经过详细的田野调查,以详实的史料和朴素的语言描述了作家生于斯、长于斯的高头村的风土人情、人文掌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晋南乡村的风俗画卷。会上,段崇轩老师提到了文学高度的问题。我想说,毕星星从乡村的村史入手,绝对做到了有深度的描写。一个乡村有完整的村史,村史中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各个方面,连粪票都不落下,足见这是一个富有文化的村庄——我们村就没有这样的村史记载,所以我写不出《河槽人家》这样的作品。毕星星从村史中,披沙拣金寻找到宝贵的写作素材,从而诞生了这部优秀的散文集。
散文,是一种门槛很低的写作形式,正因为门槛低,才拥有了广大的写作群体。事实上,门槛越低出成绩越难。就像智能手机时代,人人都会照相,都觉得自己是摄影家。会照相不一定是摄影家,会写散文不一定是作家。这就对写作素材的选择提出了挑战,什么东西能写,什么东西不能写,什么素材运用会产生好的效果,什么素材让人审美疲劳,都是需要选择和考量的。看似考验作者的眼光,其实考验的是思维能力、判断能力、艺术感觉等。当然,还有写作手法的选择,什么样的写作手法适合什么样的题材,从而实现双剑合璧的效果,这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写作题材和写作手法,本身不存在落伍或先进的问题。不像有些人特意强调写农村题材落伍了,写亲情不时髦了云云,有些编辑公开反对这类题材的写作。一看见写父爱、母爱、乡愁的文章就条件反射般弃之如敝屣。
写什么、如何写,有时候的确存在一种跟风潮。不是编辑把作者带偏,就是作者把编辑带偏。比如,某个作家打破成规、大胆地采取了一种新的写作形式,编辑眼睛一亮,觉得有创新意识,于是便追着作家要稿子,刊物不惜版面、连篇累牍地给予发表。评论家也像发现新大陆地紧追不舍,一顿夸赞,溢美之词溢于言表。别的作者就开始模仿了,一个、百个、无数个跟风。一夜之间,这种形式的文章便风靡天下。这种跟风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做法,是讨好编辑的投机取巧。我们不能妄加评论说当年所谓的知青文学、反思文学、大墙文学等文学流派产生是这种跟风所导致的结果,至少有这种嫌疑。我又想起改革开放初期,下海经商就不说了,单说农村。某个人在山里发现了一处铁矿,一村人都眼红,纷纷扛起铁镐进山找矿,庄稼也不种了。有的人确实找到了矿,发了财,有的人却空手而归,更有甚者抢夺别人的矿产。还有房地产开发,看见开发商赚钱了,不管原先做什么产业的,纷纷涉足房地产,后果大家都看见了。总之,不管做什么,一定要坚持自己,不要盲目跟风,只有适合自己的方式才是最好的。
毕星星的《河槽人家》是一部颇具社会学、历史学眼光,富有独立思考的散文力作。没有花里胡哨的炫技成分,有的只是扎扎实实的史料和真真切切的情感。由一个个个体入手,形成一个群体景观,展示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的风貌,入情入理,合情合理。在追溯历史、回望过去的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由此证明,真正的文学,一定是能够打动读者心扉、能够启迪人生的作品。写作手法当然很重要,如果能把绝妙的写作手法与精彩的写作内容完美结合,必然会产生优秀作品。
毕星星一心扑在乡村,对乡村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至少说明他热爱生他、养他的那片热土。他是一个有情怀、有担当、有责任的作家。故乡给了他生命,他以文学的形式,还故乡以热望,他做到了。所以,我们向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致敬。高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