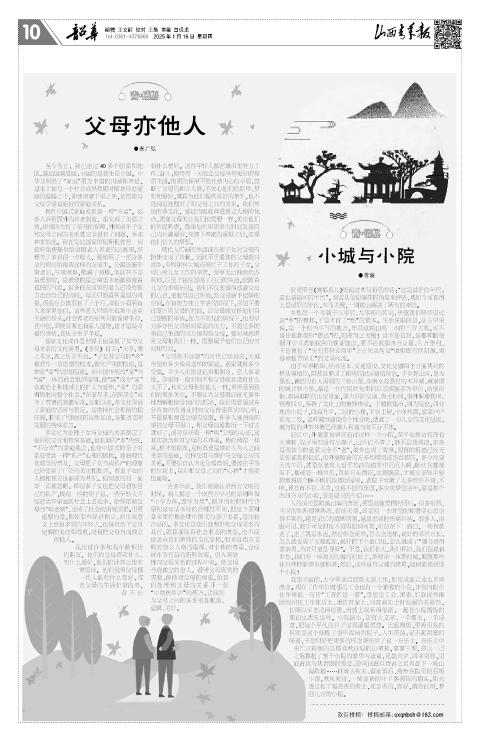小城与小院
●雪疆
狄更斯在《雾都孤儿》里说过两句有名的话:“这是最好的年代,这也是最坏的年代”。倘若从信息爆炸的角度来评估,现如今可算得上是最好的年代,车马太慢,一则微信解决了所有的牵挂。
乡愁是一个专属于八零后、九零初的名词,毕竟我们曾经见过这“乡”的模样,于是才有了“愁”的资本。生活在阳曲县,从古早里说,是一个相当牛气的地方,毕竟这两山夹一水的三晋大地,可不是任谁都敢称“首邑”的,阳曲当之无愧!且不是自封,是那种随便翻开史书就能找到的铁证如山,更不必说那四方交通、八方便利,于是便有了“先有苏村五百年”之古风余韵及“摩阳即有回阳雁,寄得南枝芳信无”的文采风流。
由于军事防御、经济往来、交通建设、文化交融四个方面共同的桥头堡地位,阳曲县形成了独特的民居建筑特色。于乡野山居,是为堡也,著名的有大盂镇的三畛古堡、东黄水故县村的木井城、黄寨镇的城晋驿古堡,都是一代代阳曲先辈们以宗族姻亲为单位,结堡而据、群居群防的历史见证,堡内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堡外铜墙铁壁、镇朔四方,保持了文化上的独特传承。于城镇集市,则为院也,四分地的小院子,四海升平,二层的小楼,下客上居,干净利落,家家户户别无二致。这种城市建设的个性分明,造就了一方儿女的文化基因,城与院的共生共舞已经融入到魂与肉不分不休。
记忆中,外婆家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小院,至于池塘边有没有大柳树、院子里有没有小燕子,已经记不清了,倒不是我薄凉,实在是现如今的老家完全不“老”,故乡也成了故事,现有的痕迹已经无法佐证我的记忆,但外婆踱着的方步和唠叨还是真切的。多少次夏天的午后,就是在老辈人近乎梵音的说笑中沉沉入睡,卧伏在葡萄架下,抑或是一株丝瓜,直到日头西沉,炊烟飘起,才被父亲轻手轻脚地将这个睡不醒的我捧回屋里。老院子承载了太多曾经不懂、不明,现在有不甘、不舍,也追不回的东西,多少次梦回童年,总是那个四四方方的小院,总是夏天的午后……
人的成长是跨越山海的奔赴,更是血脉觉醒的回归。很多东西,当时的你所惯常熟悉、看淡无感,却是另一个时空的你费尽心思也得不到的,越是记忆的清晰回溯,越是思绪的伤痛纠结。很多人,抬眼可见、触手可及时也不觉得如何可贵,可总在下一路口,一转身就走了,走了就是永远,然后你会诧异,怎么会这样,说好的来日方长,怎么就变成了天涯孤旅,说好的下个路口见,怎么就成了“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于是,我们长大,我们怀旧,我们强说着乡愁,我们在一座故去的城的旧址上,新建出一座新的城,期翼那些往日种种能够再度相逢,然后,这些没有灵魂的建筑,如何能换回那个小院?
我是幸运的,大学毕业后回到太原工作,即使成家立业也不曾改变。现在工作单位毗邻的工会也有一个雅致的小院,体制内的小伙伴常说一句话“工青妇是一家”,意思是工会、团委、妇联这些群团组织在工作性质上、团结对象上、内容联动上有很强的关联性,
长期以来走动得很勤,情感上联系得很紧,一起在小院蹭饭的
理由也就充足些。小院虽小,却有大文章,一手烟火,一手诗
意,把每个平凡的日子过得温暖惬意。比起蹭饭,更吸引我的
其实是这个像极了童年故居的院子,人生苦涩,记不起甜蜜的
味道,于是只好把更多的怀念寄托给了这一方乐土。在乐土中
央伫立徘徊的是那春秋往复的山楂树,寥寥三棵,却以一己
之躯撑起了整个小院的繁华与寂寞,花晨月夕、四季更替,见
证着我与共青团的爱恋,总向往着以青春之名奔赴下一场山
海跨越……任春去秋来、餐前饭后,漫步在院里的石板
小路,秋风吹过,一树金黄的叶子落满我的肩头,阳光
透过枝丫暖在我的脸上,花是香的,真好,就在此刻,梦
回儿时的小院。